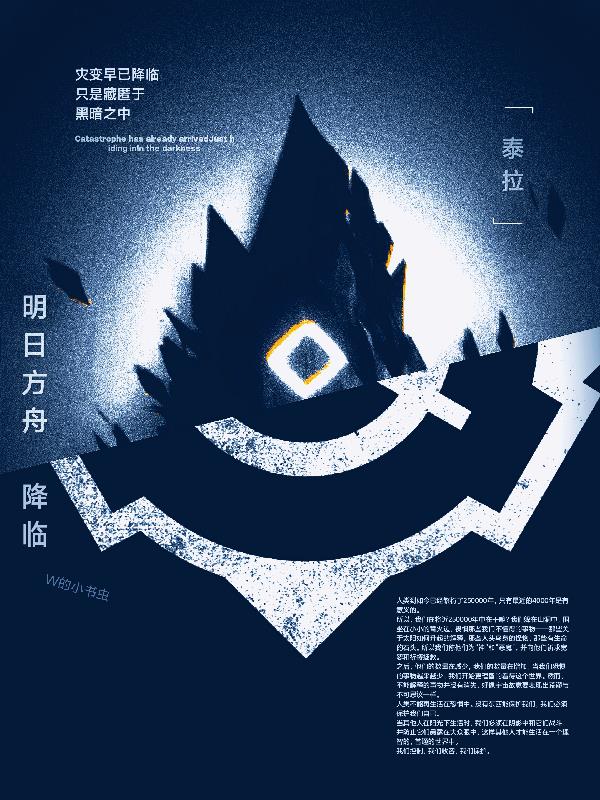孤叶浮萍第一卷泥里生东栅疯影
第十三章 第三节 那年夏天的太阳像是被谁钉在了东栅大街的上空毒辣辣地烤着水泥路面连空气都被晒得发黏走在街上能闻到旁边房屋涂的老桐油融化的味道混着远处工厂飘来的、说不清是酸还是涩的气味在鼻腔里拧成一股古怪的绳。
就是这样一个夏天东栅大街开始冒出些让街坊们私下里咋舌的事。
最先引起注意的是西街口不知从哪天起那里多了个裸着身子的男人疯疯癫癫的没人知道他打哪儿来也没人知道他叫什么。
他大多时候就坐在那块被晒得滚烫的大石头上要么对着太阳嘿嘿笑要么突然站起来光着脚在街面上晃悠步子迈得又大又急眼睛却空茫茫的像蒙着层灰。
大人们见了会赶紧把孩子往身后藏啐一口“晦气”却又忍不住在路过时偷偷瞟两眼仿佛那是幅不该看却又挪不开眼的怪画。
我那时总爱跟在几个大孩子身后在街上野从西街口往东边晃走到丰收农机厂后门就到了同学钱军良家附近。
钱军良家对门住着个女人街坊们都叫她陈金宝说是“徐娘半老”其实更像是被岁月泡得发了皱的纸眼神总是涣散着偶尔却又会突然亮一下像是藏着点什么没说完的话。
常在街上骂人有时候见着谁都会骂上几句大家都说她是疯婆娘没人愿意跟她多搭话可我和几个胆大的孩子却趁她家门没关严时溜进去看过——那可真是惊着我们了。
她家屋里暗沉沉的光线被厚厚的窗帘挡在外面可就在那片昏暗中摆着的竟是全套的红木家具。
八仙桌的桌面光可鉴人能映出我们探头探脑的傻样;太师椅的扶手雕着缠枝莲纹路里积着薄灰却掩不住木头本身的温润光泽;就连墙角立着的那个小柜子边角都打磨得圆润光滑。
我外婆家以前算是街上有点体面的可也凑不齐这样一套家什。
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败落”只觉得这疯婆娘的家像个藏着秘密的匣子外面看着破败里头却藏着亮闪闪的过去。
后来才隐约听老人说陈金宝家以前是做绸缎生意的只是后来不知怎么就败了老公她象去香港了她她象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侨民应该是在外面受了什么剌激或许是老公又娶了几房太太所以她回来了回来后人也跟着不对劲了。
再往东走在新大桥的附近张家弄口会遇见另一个疯姑娘。
那姑娘长得是真好看身量高挑穿的衣服总是洗得发白却掩不住匀称的身段。
头发有时候梳得整齐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辩子有时候又乱糟糟的可哪怕是乱着几缕发丝贴在脸颊上也显得有种说不出的俏。
街坊们说她是得了“花痴”八成是被哪个相好的或是心里偷偷喜欢的人伤着了。
没人跟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细说其中的缘由只知道她是王家的丫头。
我对她总有些莫名的好感大概是因为她哥哥吧。
她哥哥水性极好早些年夏天在运河边教过我换气他说“吸气要像饿狼叼肉猛地一口吸满沉到水里才稳当”我到现在都记得。
所以每次路过张家弄口看见那姑娘要么对着墙根发呆要么突然对着空气笑起来心里总会有点不是滋味想着那么好看的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继续往东快到流长弄附近还有一个年轻的疯小伙子名叫大观。
他是这几个里头最特别的一个——长得是真帅。
二十来岁的年纪眉眼周正鼻梁高挺哪怕是穿着件洗得发黄的旧衬衫袖口卷起来露出结实的小臂也比街上那些油头粉面的后生看着顺眼。
街坊们都说就这模样在整个东栅大街的年轻人里他要是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最奇怪的是这几个人。
按理说都是不太正常的偏偏像是约好了似的各自守着自己的地盘从不越界。
西街口的裸汉不会走到农机厂这边来陈金宝最多在自家门口晃悠王家姑娘的脚步从没出过张家弄口太远大观也只在流长弄附近打转。
有时候我特意蹲在街角观察看着他们偶尔远远遇上了也只是各自偏过头像没看见一样走开连眼神都不会碰一下仿佛彼此是空气又像是心里都揣着个默契的规矩谁也不能破。
我那时候正是爱胡思乱想的年纪总觉得这事儿透着股说不出的荒诞。
有次蹲在大观常去的那棵老槐树下看他用树枝在地上划拉着什么就凑过去跟他搭话。
我说:“大观哥你知道不?往西走点有个漂亮姐姐就在张家弄口还有个……嗯陈金宝阿姨也挺有味道的你不去跟她们玩吗?” 大观头也没抬手里的树枝继续在地上画着圈声音闷闷的:“她们脑子有问题的我才不跟她们玩。
” 他这话一出口我愣了好半天。
那语气那神情清醒得跟正常人没两样甚至比街上有些浑浑噩噩的成年人还明白。
可转脸看他继续对着地上的圈傻笑又觉得他确实是“疯”的。
这事儿就像根小刺扎在我心里好几天都琢磨不透。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文地址孤叶浮萍第一卷泥里生东栅疯影来源 http://www.xihuxs.com